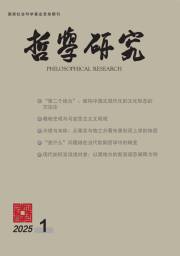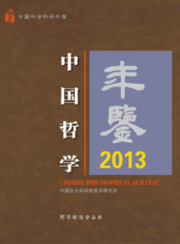首页
首页-
本所概况
哲学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 党建工作
- 研究学人
- 科研工作
- 学术期刊
- 人才培养
博士后更多+
- 图书档案
图书馆简介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 - 哲学系
【李存山】解析、综合与理论创新——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观
内容摘要: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曾被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他主张“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他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最重视解析与综合,而其所建构的是一个“新综合”的哲学创新体系。张先生以“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辩证关系为“文化之实相”,他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在他的文化观中,解析与综合的统一仍是重要的特色。盖无解析则无以综合,无综合则无以创新,这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岱年 解析 综合 理论创新
在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张先生在哲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论著,我想主要从解析与综合两个方面,谈一谈张先生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领域的理论创新。
一、解析与综合的哲学创新体系
张岱年先生在晚年曾多次表示:“自30年代以来,我的学术研究工作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二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三是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在张先生的思想中,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是有机结合、相互贯通的。
张先生在青少年时期就养成了哲人气质,他曾回忆说:“吾昔少时,有如汉代扬雄‘默而好深湛之思’,拟穷究天人之故,思考哲学问题,常至废寝忘食。”他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曾发表《评韩》和《关于列子》的文章。在读大学本科期间,他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此文受到冯友兰先生和罗根泽先生的高度评价,后被收入罗根泽主编的《古史辨》第四册。在此文的最后,张先生说:“我自己在二年前对于考证发生过兴趣,现在却久已离考证国土了,并已离开古书世界了。”这说明在张先生读大学本科的后期,他主要转向了对现代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但从后来发表的研究成果看,特别是从他在193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看,他的哲学理论研究实际上也一直是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根砥。
在哲学理论研究方面,张先生早年在其兄张申府先生的引导下,研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尤其是新实在论者如罗素、穆尔、博若德、怀特海等人)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新唯物论的著作。他在1933年初发表的《哲学的前途》一文中说:“现在的世界的哲学界,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错综纷乱的局势。种种不同的派别在互相角逐,互相抗争着。”“在本世纪之初。进化论派的哲学大盛一时,在法国有柏格森(Bergson)的创造进化论,在美国有詹木士(James)的实用主义。”“旧唯心论的余势,及这二派哲学大盛的结果,乃引起了新实在论的反动。在英国有穆尔(More)、罗素(Russell)、亚历山德(Alexander)等……于是实在论大盛。”“但不久美国又出现了批评的实在论……”“正在这些学派相斗争的时候,在德国又异军突起了一派,就是胡萨尔(Husserl)的现象学……”“怀梯黑(whitehead)由实在论者一转而提出一种有机主义,也予思想界以大的影响。有很多人认为,胡萨尔的现象学,与怀悌黑的有机哲学,乃现代哲学中两个最宏伟的系统。”在这篇文章中,张先生先后列出了当时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提到了近三十名西方现代哲学家。正是在对西方现代哲学进行解析和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不相信将来哲学要定于一尊……但我相信,将来哲学必有一个重心或中心。”“这为将来世界哲学之重心或中心的哲学”当有三个特点:“一、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二、辩证的或反综的”;“三、批评的或解析的”。
在1933年4月发表的《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张先生一方面肯定“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另一方面又认为:“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实只雏形,完成实待于将来。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学。”“现在形式之新唯物论所缺之者实为解析方法,而罗素哲学则最能应用解析方法者。”
张申府先生在1932年10月22日《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编余”中提出“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张岱年先生则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说:“吾以为将来中国之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
1933年秋,张岱年先生在北师大毕业,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推荐,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他在1935年3月发表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中,将哲学的发展创新与“民族复兴、文化再生”联系在一起,指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首先“必须是综合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时对于西洋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其次,它必须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复次,“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更次,它“必与科学相应不违”。为满足这四个条件,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在内容上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辩证)的和批评(解析)的。
1935年11月,孙道升在《国闻周报》发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其中说:“新唯物论亦称辩证唯物论”,它在中国分为两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袭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张申府、张季同、吴惠人等先生可为代表”。这里所说“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标识了张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即他重视逻辑解析,是要“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以实现辩证法与解析法相结合。
1936年5月,张先生发表他早年哲学思想的一篇代表作,即《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在此文中,他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并且从方法论、知识论、宇宙论、人生论四个方面提出了“新的综合哲学之大体纲领”。
继此之后,张先生在抗战期间写了一部分“研思札记”,在40年代写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五部哲学论稿,此即后来所称的《天人五论》。张先生晚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撰写这些论稿,意在实现‘将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构想”,又曾说他晚年在哲学上“仍坚持30至40年代的一些观点而略有补充”。
张先生晚年总结自己的哲学思想,还曾作有《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新综合哲学要旨》一文。他说:“我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法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三者结合起来,以分析为方法而以综合为内容,可以称为新综合哲学。”
根据以上所述,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最重视解析(分析)与综合,而其所建构的是一个“新综合”的哲学创新体系。
二、解析与综合的文化创新论
张岱年先生对中国文化问题的研究始于他在1933年6月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1935年1月,上海的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张先生参与当时的文化讨论,于同年的3月和5月发表了《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和《西化与创造》两篇论文,提出了“创造的综合”或“文化的创造主义”等观点,并精辟地指出:“惟用‘对理法’(按即辩证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才不失之皮毛,才不失之笼统。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在这里,张先生讲了关于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三对辩证关系。“整”是指文化的系统性,“分”是指文化要素的“可析取性”,所谓“析取”就是解析(分析)和择取,这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解析和择取;文化的“变与常”是指文化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与继承性、连续性;文化的“异与同”则是指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与世界性、普遍性。
关于文化的“变与常”,这是张先生文化观的一个核心观点。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文化以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力发展到一新形态,社会关系改变,则文化必然变化。”这显然是唯物史观关于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其强调了文化之“变”。张先生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现在要仍照样保持中国的旧文化,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张先生又把语势一转,提出:“中国的旧文化既不能保持原样,那么,是否就要整个地将其取消呢?将其扫荡得干干净净呢?不!只有不懂唯物辩证法的人,才会有这种主张。”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传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来,对其简单化、机械化的一个理解就是只讲文化之“变”而不讲文化之“常”,认为文化“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当进入工业社会时,原在农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中国旧文化就已完全不适应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当“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时,“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张先生在文化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把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恢复了唯物史观在文化理论上的“活的灵魂”,对于要把中国的旧文化“整个地取消”、“将其扫荡得干干净净”的观点提出了断然的否定,指出“只有不懂唯物辩证法的人,才会有这种主张”。而张先生的一个新见就是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必然变化”,但是“变中有常”。
张先生说:“文化是发展的。文化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有变革,而且有飞跃的变革。但是文化不仅是屡屡变革的历程,其发展亦有连续性和累积性。在文化变革之时,新的虽然否定了旧的,而新旧之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所谓文化“有飞跃的变革”,就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如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则文化的发展亦有阶段性,有“飞跃的变革”,所谓文化之“变”主要指此。张先生又把语势一转,指出“文化不仅是屡屡变革的历程,其发展亦有连续性和累积性”,在社会发展进入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文化变革之时,新的虽然否定了旧的,而新旧之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此“连续性”就是文化之“常”。
关于文化的“异与同”,这也是张先生文化观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两个生产力发展程度相同的民族,由于地域之不同,其文化虽大致相似而仍不相同,这从世界的各民族以及近世欧洲各国的历史可以看出。”“民族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各历史阶段所有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然而世界性不是无民族性。”这里所说的“世界性”即是文化之“同”,而“民族性”即是文化之“异”。文化之“同”是蕴含在各民族文化中的普遍性,而文化之“异”就是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只有同时承认这两方面的存在,才不是“以偏赅全”。
依据文化的“变与常”、“异与同”的辩证关系,张先生说:“要保持旧文化,不思与世界文化相适应,结果必归于绝灭而已;同时,如根本唾弃本土文化,要全盘承受外来文化,亦终必为所同化而已,其自己的文化也一样归于绝灭。所以,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张先生既反对全盘西化论,又反对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旧文化之复活”,其理据就在于对文化的“变与常”“异与同”之辩证关系的认识。
关于如何认识文化的“变与常”“异与同”,实际上都是以承认文化系统要素的“可析取性”为基础或前提。张先生说:“无疑地,中国文化之过去阶段已经终结,中国必踏入文化上的新阶段,那么,还要保持旧的特点吗?……中国文化中,是不是有些特点,并不只是农业文化的特点,而是一种根本的一贯的民族的特殊性征,在农业时代前本就存在,在农业时代后仍可存在?”在这里,张先生要区分中国文化在农业社会的特点与中国文化的跨时代的“根本的一贯的”民族文化特殊性。而后者也正是张先生所强调的中国文化之“常”或中国文化之“异”。
张先生要区分中国文化在农业社会的特点与中国文化的跨时代的民族文化特殊性,这就势必要对中国原有的文化进行分析。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种文化中必然含有相互对立的成分,即好的或较有积极意义的和坏的或具有消极意义的成分。唯物辩证地对待文化,就应一方面否定后者,一方面肯定前者,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发挥、充实。”他在《西化与创造》一文中也说:“由‘对理’来看,文化固是一个整体,而亦是可分的。”“文化并无不可分性,而是可析取的。文化各要素,并非都有不可解的必然联系。”此即张先生的文化之“整与分”的辩证观点。
一个民族的新时代的文化可以析取前一时代文化系统中的积极成分,亦可析取其他民族文化系统中的优长因素。在这里,承认文化之“整”的系统性已是司空见惯,而许多人因文化的系统性而否认文化是“可析取的”。这貌似对文化持一种系统的“活”的见解,而认为如果把文化系统中的某些要素析取出来,它就已经“死”了。然而实际上,文化之所以是“活”的,就在于它是可以“吐故纳新”的。如果旧文化系统只能保持原样,“不思与世界文化相适应”,不能与现代文明相协调,那它在新的时代就已经“死”了。如果其他民族的文化也是一个不可分的系统,那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也就不能进行相互交流,只能是要么全盘排拒外来文化,要么全盘接受外来文化。张先生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是“死路一条”。因此,文化必须既讲“整”又讲“分”。只有这样,文化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中有常”,也才能既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又能实现文化的现代性。
张先生提出的文化之“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观点,的确是“文化之实相”。我认为,迄今为止,尚无其他的观点能过之,这仍是一个对文化的最深刻、最全面、最正确的见解。若要对文化有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或者说对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那么,这几个方面都缺一不可。盖有“分”而无“整”,则对中国文化的系统性缺乏认识;有“整”而无“分”,则中国古代文化只能保持原样,或只能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有“常”而无“变”,则中国古代文化亦只能保持原样;有“变”而无“常”,则不能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同”而无“异”,则否认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有“异”而无“同”,则把中西文化绝对对立起来,二者之间不能相互交流。这几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张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化的“创造的综合”,以及他在晚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实际上都是立足于这一文化的辩证发展观。如他在晚年所作《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更新》一文中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条是“民族文化的积累性与变革性”,此即文化的“变与常”的观点;第二条是“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和矛盾性”,此即文化的“整与分”的观点;第三条是“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主体意识”,又在《关于文化问题》一文中说“中西文化的异同都是相对的……现在讲中西文化的异同,既要注意相异之处,也要注意相同之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此即文化的“异与同”的观点。
张先生在晚年所作《文化体系及其改造》一文中讲“文化的体系及其层次”,然后讲“文化体系内部的各种联系”,而在各种联系中,文化各元素之间“有可分离的关系和不可分离的关系,有相容的关系和不相容的关系”。此中所讲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就是在《西化与创造》一文中所说“有些要素有必然关系,必须并取”;而“可分离的关系”,就是在《西化与创造》一文中所说“有些要素则无必然关系,却可取此舍彼”。张先生举例说,科学与思想自由是不可分离的,故而二者必须并取;而科学与基督教是可分离的,故而可取此舍彼。关于“相容的关系和不相容的关系”,张先生举例说,平等思想与等级思想是不相容的,思想自由与专制主义也是不相容的,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而“事实证明,二者是相容的”,“儒家思想中有跟经济发展相容的部分,也有不相容的部分”。作出这些分析,实际上就是关于文化之“整与分”的理论展开,其与文化的“变与常”“异与同”的观点一起,构成了张先生晚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基础。
在张先生的文化观中,解析(分析)与综合的统一仍是重要的特色。盖无解析则无以综合,无综合则无以创新,这对于当今如何认识文化的“古今中西”的关系,如何既坚持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又要使中国文化适应世界普遍潮流的现代性,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创未来”,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社科期刊网》微信公众号)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 电话:(010)85195506
电话:(010)85195506
![]() 传真:(010)65137826
传真:(010)65137826
![]()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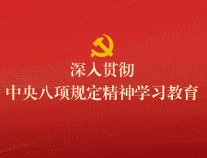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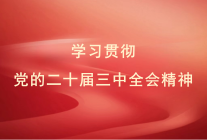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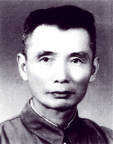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