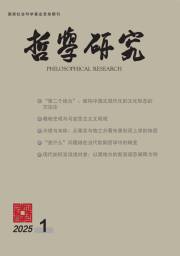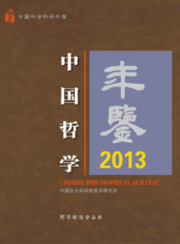【王齐】运动中的真理:从克尔凯郭尔到尼采或福柯的尼采
【摘要】多元普遍主义是普遍主义概念在全球化的、技术化的和多元文化的当今时代的应有之义。与之相应,多元普遍主义哲学图景之下的真理将不再以绝对真理或“大写的真理”的面目出现,而将呈现为多元、多重的样态。为保证这样的真理不陷入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泥淖,必须破除现代性所划分的清晰界限,允许真理具有多义性、边界的模糊性、不可预测性。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或许在于令真理运动起来,不仅每一种真理要处于自我生成的进程之中,而且多元、多重真理之间还要通过互相观看、互相质疑的博弈令自身处于生成和变化之中,使每一种真理都有可能进行自我校正,防止真理终结为教条或安然固着于特殊性。这种从绝对真理向运动中的真理演变的可能性可由克尔凯郭尔对西方哲学史上两条真理道路的揭示以及尼采或福柯的尼采的真理观来加以证明。
【关键词】多元普遍主义;相对主义;真理;运动
本文是对《普遍主义的迷思及“出路”》的接续思考。在该篇文章中,笔者尝试借助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的《圣保罗:普遍主义的基础》和荷兰政治学家斯图尔曼的《发明人类》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绝对知识与地方知识之间无法消解的二元紧张关系的揭示,论证作为哲学理想的普遍主义实际上都是有限度的普遍主义。因为提出每一种普遍主义哲学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人不具备全知全能的神视角,即便“思想的无限运动”的力量有能力突破个人所受的时空限制,这种突破终究是有限度的。既然所有的普遍主义都不够普遍,那么,“多元普遍主义”或者如赵汀阳所说的“兼容性普遍主义”就有可能成为有效的普遍主义。如果上述观察和分析有其合理性,那么紧接着需要考察的便是多元普遍主义哲学图景之下何谓真理的问题。自真理与意见之分在古希腊出现以来,哲学家一直警惕相对主义,担心相对主义会使意见泛滥,甚至成为错误思想的掩体。为防止相对主义借多元普遍主义泛滥,本文尝试提出“令真理运动起来”的思想方案,从西方哲学史上以希腊和希伯来文化为标识的两条真理道路入手,围绕克尔凯郭尔、尼采或福柯的尼采对真理问题的分析,论证从绝对真理向动态的、永无终结的真理观演变的可能性。
一、引子:多元普遍主义的哲学图景
在开启新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多元普遍主义”这个说法及其所蕴含的哲学理解和哲学方法论进行补充论证。
“多元普遍主义”是对“普遍主义”这个古老概念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的解释说明。“普遍主义”对应的英文词universalism出自universe。根据剑桥大学古代哲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大卫·赛德利的观点,从定义上讲universe只有一个,没有复数形式,它对应于希腊词to pan,意为“全有/大全”(the all),其含义为“所有存在的东西,尽管这通常会排除无时空性的东西,比如数字”。问题是,这种“大全”视角是神视角,不为人所有。现代哲学家如黑格尔忘记了人的有限性,他所构建的思辨的绝对哲学体系将自身等同于神,而这种隐含的神视角被“黑格尔之后”的代表性哲学家之一克尔凯郭尔揭穿了。当克尔凯郭尔提出“生存本身就是一个体系——为上帝而在,但却不为任何生灵而在”的时候,他明显是在指责思辨哲学家忘记了人神之间的绝对差异。在人作为个体的问题上,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显然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将人视作单独面对神的“单一者”,极言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人神存在绝对差异的前提下,他所说的个体最终只是一个“可怜的生存者”,而只有神才有资格成为“既在生存之外,又在生存之内”的“体系思想家”。在克尔凯郭尔之后,持有视角主义真理观的尼采在“上帝死了”的背景之下不甘心做一个“可怜的生存者”,他向生命本身提出了不断进化甚至永恒复返的要求——生命将不断克服自身,向上攀登,使作为“桥梁”的人成为“超人”。尼采清楚地意识到了人观看世界时所带有的定点透视的特点,但他通过“登高”意象坚毅地表达出他突破中心透视的缺陷的决心。这里我们举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漫游者》当中的一段话:
为了观看大量,就必须学会撇开自身:这样一种坚强是每个登山者所必要的。
然而,谁若作为认识者以自己的眼睛而纠缠不休,则对于万物,除了它们的表皮原因,他怎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可是你,查拉图斯特拉啊,你却意愿观看万物的基础和背景:所以你就必须上登,越过你自己,——上去,上升,直到你的星辰也落在你之下!
可以说,尼采的视角主义绝不意味着人只能居于柏拉图的洞穴之中。相反,视角主义的应有之义就是多重视角的并存与兼容,视角主义终将通达多元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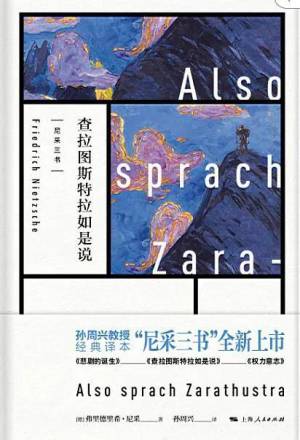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如果说,克尔凯郭尔洞悉到了思辨哲学传统中隐含的神视角并对哲学家忘记人神差异的现象感到愤愤不平,尼采从人自身的进化和改造着手开启了多视角主义并存的可能性,那么,法国当代哲学家提出的“差异”概念不仅能够使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哲学努力之意义更加清晰,而且还有可能替代现代哲学当中其实不够“大全”的、有限度的“普遍”概念,成为更为有效的解释生活的概念。海德格尔说过,哲学起源于实际生活经验,然后又会跳回到实际生活经验之中。在哲学与实际生活经验之间的往复关系的完成需要概念的创造,这是哲学的根本工作。哲学概念的创造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正如福柯曾经指出的,在考察哲学的“概念需求”(conceptual needs)之时,我们需要了解激发我们进行概念化的历史条件,“我们需要有对于我们当下境况的历史意识”;另外,还需了解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实在”(reality)的种类。福柯此言告诉我们的是,每一个哲学概念都有其历史有效性。在柯尼斯堡按部就班地生活了一辈子的康德从纯粹理性出发所构想出的以自由为“拱顶石”的哲学体系,其普遍性在他所处的时代乃至当代都有其有效性,只是对于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仅从经验出发就不得不思考多元主义的今人来说,康德哲学的普遍性究竟有多普遍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康德哲学的普遍性,而是想说明,康德哲学并不是唯一的普遍哲学。只要我们承认人非全知全能,那么普遍主义的应有之义就是多元普遍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现代哲学的特征是借助理性的“建筑术”以构建拥有某种“拱顶石”的体系,那么当代哲学则以多重“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的彼此并存、相互交织的立体图景为特征,其中,每一个“内在性平面”都是“混沌”的切面,每一个“内在性平面”都是一个“大全”(One-All),每一种哲学都是普遍的哲学。
接下来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一个令很多人担心的问题:多元普遍主义哲学会导向相对主义吗?有此担忧的人或许首先需要思考自以为“大全”但实则有限度的普遍主义哲学导向绝对主义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如此,问题似乎出在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这样的对偶概念之上,它们很容易陷入黑格尔所指出的非此即彼式的旧形而上学独断论,这是“思想的无限运动”的不幸。为走出思维的死胡同,我们需要如福柯所说的新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tools),比如德勒兹和巴迪欧讨论过的“独特性”(singularity)概念,或许就有可能突破“普遍”与“特殊”的简单二元对立所造成的思维僵局。不管“独特性”是否可以被称为新的“概念工具”,至少我们应该明确,如果承认人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是有限度的,那么普遍与特殊、绝对与相对之间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应被摒弃。
多元普遍主义是适应于全球化的、技术的和多元文化的当今时代的思想主张,与之相应,哲学的真理观也应做出调整。在多元普遍主义哲学图景之下,真理不再可能固执一端而成为绝对真理或“大写的真理”,真理将呈现出多元、多重的样态。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思的是,把欧洲疾病的根源归结于柏拉图主义的尼采通过分离知识与意志、通过视角主义开启了多元真理的方向,而主张“必须坚定不移地治愈反柏拉图主义的病症”的巴迪欧也对多元真理的可能性做出了论证。巴迪欧认为,为满足时代的需要,需要新的真理理念。通过“类性多元”概念的创造,巴迪欧开启了“多的柏拉图主义”,主张“存在是多,真理也必须是多”,以此来应对哲学终结的论调。
需要强调的是,倡导多元、多重真理绝不是要导向不知是与非或者不能做出是与非的评判的相对主义,那种做法无异于向“混沌”的回返。更为重要的是,特殊性、差异性永远都不能成为错误思想的庇护伞。多元或多重真理的旨要在于破除现代性所划分的清晰界限,允许真理具有多义性、边界的模糊性、不可预测性。如何做到这一点?美国后现代哲学家卡普托在其《真理》一书的“导论”标题中所说的“运动中的真理”(truth on the go)很有启发性,本文的写作亦受益于这本书。让真理运动起来,不仅每一种真理要处于自我生成的进程之中,而且多元或多重真理之间也要通过互相观看、互相质疑的博弈令自身处于生成进程之中。有生成就有变异,有变异就有了自我校正的可能性,如此真理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终结为教条。
那么,真理能否运动起来,以及如何运动起来呢?下面笔者将从对西方哲学史上两条真理道路的考察入手,论证令真理运动起来的可能性。
二、从永恒真理到运动中的真理:一个哲学史考察
当德尔图良发出“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的质问时,西方哲学和思想史上两条真理道路的对立就不再是新鲜事了。但由于德尔图良具有鲜明的护教论立场,耶路撒冷的真理之路很难与信仰之路相区分,因而这条真理之路很难为哲学所接受。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克尔凯郭尔1844年出版的《哲学片断》一书以思想试验的方式清晰地揭示出了与希腊的“回忆说”迥异的希伯来的“道路真理”说,并且其在两年后出版的《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一书中为后者赋予了生存论的意涵,使得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对立真正成为两条不同的哲学真理道路的对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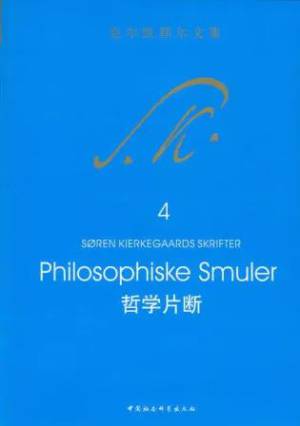
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断》,王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让我们首先对《哲学片断》的内容进行一次重构。《哲学片断》开篇即从“美德是否可教”这个“苏格拉底问题”出发,提出了“真理是否可教”的问题。根据苏格拉底的观点,回答“美德是否可教”的关键在于美德和知识是不是关于善和知识的原则。如果美德和知识作为原则而存在,它们就是普遍可传达的,因而是可教的。这种知识的普遍可传达性的结果就是“回忆说”:所有的知识和美德都是“在先存在”的,它们原本根植于求知者的心中;求知者只需要被提醒,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回忆起曾经知道的知识。虽然知识和真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教师的存在仍有其必要性。教师的作用不是给予学生知识和真理,而是提醒学生去回忆,启发、开导学生自己思考,向自身内部沉潜。这也就是苏格拉底把教师定位于“助产士”的原因,因为在他看来,“生产”是神的事。在“回忆说”的思想视域之下,每个人都得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与“回忆说”旨趣迥异,克尔凯郭尔提出了一个试验性的“思想方案”。其中,从学生的一面来说,学生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学生就是“非真”(Usandhed/untruth)。在伦理的意义上,“非真”就是“不老实”,在宗教的意义上就是“罪”,后者正是克尔凯郭尔所强调的。而从教师的一面来讲,“思想方案”中的教师必须亲自把真理和理解真理的条件带给学生;教师需要提醒学生,其“非真”是由自身的“罪过”所致。因此,教师不是在教导,甚至不是在改造学生,而是在对学生进行再塑造。如此,克尔凯郭尔说,这样的教师只能是“神”,虽然他以思想试验的手法把“神”写为“Guden/the God”,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Gud/God”,但从这位教师被称呼为“拯救者”“解放者”“和解者”“法官”的事实来看,从《哲学片断》第二章以诗化手法所描摹的“神”在人间的受难故事与福音书之间的同构关系来看,尤其是从全书结尾“寓意”部分所强调的“思想方案”的诸关键词“信仰”“罪的意识”“瞬间”“时间中的神”来看,这个“神”就是基督教当中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在《哲学片断》中,克尔凯郭尔极力回避给他的“思想方案”披上基督教这件“历史的外衣”,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看出,这个“思想方案”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的翻版。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基督教的语境之中,那么不仅《哲学片断》的思想价值要受到怀疑,而且我们也完全可以站在希腊哲学的立场上对“道成肉身”式的真理之路提出质疑。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但他并没有办法作见证,只能采用被法利赛人一眼看透的自我见证法,说:“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约翰福音》8:14)在哲学家眼中这种辩解无异于独断。当耶稣被抓捕后送到罗马总督彼拉多面前受审时,彼拉多问他:“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而彼拉多反问:“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18:37-38)这里暗含着对由信仰所通达的真理之路的不信任。尼采接续了这种不信任,他以明确无误的方式把“信”与“真”作为两条道路对立起来。尼采认为:“真理和相信某些东西是真理:这是两个界限分明的兴趣世界,两个几乎对立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才把彼拉多视为《新约》中唯一必须尊敬的人物,因其看穿了耶稣对“真理”概念的滥用。
为了应对尼采的批评,更为了使克尔凯郭尔所揭示的“道成肉身”的真理道路能够真正成为与“回忆说”相对的另一条真理之路,我们需要把他一直犹豫着是否为“思想方案”披上的那件“历史的外衣”剥离下来。克尔凯郭尔的犹豫有其考虑,那就是要把人们早已烂熟于心的基督教教义陌生化,打破在基督教大获全胜的时代早已程式化的信仰,为信仰重新注入激情。但这件“历史的外衣”对于本文的目标而言就是一种障碍,如果不剥离掉它,“道成肉身”的真理之路就只是一条特殊的真理之路,它不能向所有人敞开。所幸克尔凯郭尔反讽的写作策略再次奏效。从《哲学片断》到《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随着基督教这件“历史的外衣”渐渐明朗,“道成肉身”的真理之路也逐渐开显出了其独立于基督教的生存论意义。“道成肉身”,神在时间中降临于世,意味着“永恒真理在时间中生成”,意味着“永恒的、本质的真理不是在他身后,而是自己通过存在或者已然存在的方式走到他前面”。而如果永恒真理已经在个体的前方,那么真理就不再是思想的对象,而应成为个体行动的目标。个体若要抓住真理,就只能通过在时间中与真理建立关系的方式来实现,因为“回忆的后门永远地关上了”,个体不能后退,只能向前,在时间中以生存的方式抓住真理。当克尔凯郭尔道出“回忆的后门永远地关上了”之时,他的参照系显然是“回忆说”。真理在时间中生成,这意味着没有可供回忆的现成的真理,真理是动态的——它总是在某个瞬间生成;更意味着个体与真理的关系是动态的,个体将永远处于“占有”真理的过程之中,就像克尔凯郭尔在《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中列出的“莱辛命题”所说——假如上帝把全部真理置于右手,把向着真理的不懈努力置于左手,他将谦卑地选择那只左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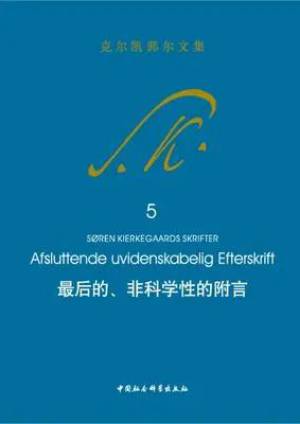
克尔凯郭尔:《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王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至此,克尔凯郭尔完成了对“道成肉身”的真理之路的去历史化、去特殊语境化的处理,并且令个体的生存处于运动状态。克尔凯郭尔对生存做出了如下定义,他说:“何谓生存?生存就是无限和有限、永恒与时间所生的那个孩子,因此它持续地奋斗着。”如果生存是一场持续的斗争,那么真理就真的成了“道路”,而不是耶稣自我宣称的“道路”;“道路真理”永远处于运动之中。遗憾的是,克尔凯郭尔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概念王国,他采用的“概念工具”仍然是黑格尔式的,在真理问题上亦没有摆脱“主观—客观”的概念框架,这就给自己的理论造成了不少麻烦。比如,他把真理定义为“通过最具激情的内心性在占有之中牢牢抓住的一种客观不确定性,这是对一个生存者来说的至上真理”。也就是说,从客观的角度说,真理是一种“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强化了主体的内心性的激情,使得主体对真理的追求成为一种面对客观不确定性的冒险。如此,克尔凯郭尔关于真理的定义又将处于被拉回到对信仰的重述的危险之中。或许只有抛开“主观—客观”这套“概念工具”,才能彻底完成克尔凯郭尔对“道成肉身”的真理之路的生存论改造,使“道路真理”处于运动之中。
在《哲学片断》中,克尔凯郭尔还强调了“瞬间”对于信仰和生存的意义。当真理不再是现成的、可供回忆的真理之时,当真理要在时间的某个点上“降临—生成”之时,这个点就成为“瞬间”,克尔凯郭尔称之为“决断”,没有这个“瞬间”,一切都将返回到苏格拉底。换言之,“瞬间”是“道成肉身”的真理之路与“回忆说”相区别的关键。至于“瞬间”将以何种方式来临,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只是引用《马太福音》第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提醒人们保持对于真理“降临”的警觉。值得一提的是,“瞬间”降临的问题落在了海德格尔的思想视域之中,保罗在《贴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2节中所说的“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句话引起了海德格尔的重视。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在时间中的“降临—生成”的“瞬间”就是kairos(时机),时机的到来是突发且不可预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真理的“降临”定位于“生成”,那么仅有警觉是不够的,这里还需要引入意志和创造,这是尼采的问题。为了继续本文的讨论,我们将引入福柯的尼采解释,因其更清晰地凸显了尼采的哲学意图。当福柯把亚里士多德和尼采作为求知意志的两种范式的时候,当他强调权力意志是知识与真理之间的断裂点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意志完成了从“存在”向“生成”的转变,因而更靠近本文的论题。
福柯在1970—1971年法兰西学院课程的《求知意志讲稿》中,从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那段“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的文本(A1,980a)入手,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知识和欲望不是处于两个不同的场所,不是为两个主体或两种权力所拥有;相反,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渴望知识的人就是占有知识或者有能力占有知识的人,渴望知识的人终将获得知识,其间不需要“暴力、占有和斗争”,而只需依靠和实现人的自然本性。根据福柯的分析,尼采是第一个使求知欲望与知识相分离的人,“尼采重建了被亚里士多德取消的距离和外在性”。因为这种“取消”持续存在于西方哲学史中,尼采此举相当于挑战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一旦“距离和外在性”被建立起来,知识和真理之间的纠缠就被解开了——知识不以真理为目的,真理也不是知识的本质;求知和求真活动也被置于运动和过程之中。又因为尼采挑战的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传统,他给出的路径可以轻松摆脱克尔凯郭尔身上那种不时向信仰之路回返的危险。
在1971年4月的麦吉尔大学“尼采讲座”中,福柯强调了尼采关于认识和真理是人的发明的观点。福柯指出,在尼采看来,认识不是人的本性,认识没有模型,没有像“神圣理智”这样的外在保障,因而也“没有回忆说”——知识是一种“复杂操作”的产物。福柯的总结很容易让我们与尼采反柏拉图、反“背后世界”、不承认有本质或真理躲在现象背后的哲学立场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之上,福柯还摘引了尼采的《快乐的科学》第109节的部分内容,并且改动了皮埃尔·克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通行法译本,因此这里不是直接引用《快乐的科学》,而是根据福柯的摘选对尼采的思想主旨进行重述。在尼采眼中,世界本是“混沌”,自然界没有法则、没有目的。通过强调认识和真理是人的发明,尼采希望把世界、自然和人彻底从“上帝的阴影”之下解救出来。福柯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尼采的两个“不合时宜”的思想:首先,知识出现之前没有同谋,没有权力的保障,“知识从完全不同的东西里涌现”;其次,“真理的出现出乎意料”,真理的涌现无关“真”和“非真”的区分。这两个“不合时宜”的思想可与前文的讨论在两点上相关联。第一,真理“涌现”的不可预测性。因为不可预测,克尔凯郭尔将真理的“涌现”视作“奇迹”,此语差不多指向了《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中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又一次表现出了向信仰回返的倾向。相比之下,尼采是把突然“涌现”的真理当作“礼物”。既然是“礼物”,真理的给予者就既无法要求“礼物”被欣然接受,亦不应求回报。这一点能够解释为什么查拉图斯特拉在下山伊始便向世人宣称“我要带给人类的是一件礼物”,并且否认自己是在“施舍”;同样,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在市场上首次宣讲“超人”学说时受到了群众的无情嘲弄,他们大叫着要求查拉图斯特拉把“末人”给他们。尽管“礼物”可能不被接受,但查拉图斯特拉仍然把“赠予的德性”视为“最高的德性”。
第二,“非真”(non-vrai/not-true)之说与《哲学片断》中所说的学生在接受真理之前所处的“非真”(Usandhed/untruth)状态可相呼应。在没有剥离掉基督教那件“历史的外衣”之前,克尔凯郭尔认为“非真”是“罪”,若想摆脱“罪”,必须依靠教师亲自给予学生真理以及理解真理的条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柯的尼采的“非真”状态摆脱了“上帝的阴影”,尼采的“非真”既非真亦非不真,它异于传统的真与非真的分类。这个意思是说,真理不是现成的、可符号化的并因而普遍有效的“什么”,真理的“涌现”也不是从“非真”到“真”的纠错或改过过程;真理是一种创造,从无到有的创造,没有终点的创造。创造的意义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有突出的表现,例如“三种变形”中查拉图斯特拉不仅为狮子设定了目前能够达成的“为自己创造自由”的目标,而且还设定了狮子尚无法达成的“创造新的价值”的目标。至当代法国哲学家,尼采所言的创造被具体化为福柯所说的“复杂操作”,或者巴迪欧所说的“真理程序”。
至此,我们以真理为主线,还原了从克尔凯郭尔到尼采和福柯的尼采的思想演进历程。从克尔凯郭尔对“道路真理”与“回忆说”的对立开始,到他对“道路真理”的生存论意义的揭示,再到尼采对知识与意志的分离,真理不再恪守其永恒不变的面貌,而是处于不断的生成和运动之中。德勒兹说过,运动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全部著作的真正主题,本文对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真理观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判断。
当尼采把真理视为创造之时,“事件真理”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而尼采作为本文论证的内在线索这一点也得到了证明。尼采对于当代法国哲学的影响已无须多言,福柯和德勒兹均参与了科利和蒙提那里《尼采全集》法文版的工作。当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提出“内在性平面就像是混沌的一部分”的观点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尼采《快乐的科学》第109节的回响。除了把尼采作为重要思想资源之外,德勒兹、福柯以及巴迪欧都十分欣赏法国诗人马拉美“所有思想都在骰子一掷中涌现”的意象,在生活中他们也身体力行,针对时代问题持续发声,主动创造“哲学剧场”的效应,在动态之中尽显真理的创造性,最终在实践层面上完成了从永恒真理向运动中的真理的转变。
三、余绪:从追寻真理到对真理的爱
卡普托在《真理》一书中对后现代的哲学图景进行了形象的描绘。与现代世界所呈现出的中心化、数学化、体系化的世界图景相比,卡普托认为《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用“chaos”(混沌)和“cosmos”(宇宙)合并造出的“chaosmos”(混宇宙)一词能够用来描绘后现代的世界图景,因为这是“一种秩序与混乱的最佳混合:恰到好处的秩序以避免陷入混乱,恰到好处的混乱以使系统向着新奇效果、向着创新和再创造开放”。这里我愿意做一个增补。如果我们考虑到古希腊语“kosmos”表示“有序宇宙”且并不限定在单数中使用的事实,考虑到“chaos”的字面意思同时包括“豁开的空间”和“无序的流动”的事实,那么这个“chaosmos”(混宇宙)的描述就完全可以被视为对德勒兹所构想的多重“内在性平面”相互交织的立体图景的一种有力解说。顺此思路,卡普托自己也造出了“chaosmopolitanism”(混沌世界主义)一词作为后现代图景的理想型,认为这种理想型可用相对论、量子物理学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来佐证。于是乎,跟此前神视角下的真理和纯粹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理相比,后现代真理就是“事件真理”,即紧密围绕“事件”生发,后者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缺乏清晰可辨的原因或坚实基础的特性,使得“事件真理”必定是“去中心化的”(decentered)——借用巴迪欧的术语,是不确定的和无限开放的,真理在根本上成为一桩冒险的事业。

John D. Caputo, Truth, Penguin Books, 2013
当“冒险”一词出现之时,克尔凯郭尔以及他所推崇的莱辛的影子再次闪现。在克尔凯郭尔的定义中,真理不仅是一桩冒险的事业,其性质还与信仰相同。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永恒福祉”是最大的不确定性,但值得个体舍弃一切去追求,“一桩冒险事业并不是一个浮夸的词藻,不是一个感叹语,而是一桩艰苦卓绝的工作;一桩冒险事业,不论它多么胆大妄为,都不是嘈杂的宣称,而是安静的奉献,它知道,它事先得不到任何东西,但却要拿一切去冒险”,因为相信者相信,上帝不会放弃他。透过克尔凯郭尔,我们听到的是帕斯卡尔的声音——赢就赢得一切,输却一无所失;当然还有新教路德宗的“因信称义”作为其内在支撑。但是如果事情仅止于此,那么我们可以再次怀疑克尔凯郭尔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当克尔凯郭尔在《哲学片断》中说出“任何一种激情的至上力量总是希求着自身的毁灭,同样,理智的最高激情也要求着冲突,尽管这冲突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理智的毁灭。去发现某个思想所不能思考的东西,这就是思想的最高形式的悖谬”的时候,他已成为卡普托眼中标准的“后现代预言家”。在这个方面,尼采岂有落后之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在《创造者之路》中表达了为创造而不惜以毁灭自身为代价的勇气——“你须意愿在你自己的火焰中焚烧:如若你没有先化为灰烬,你怎能新生!”对于始终处于生存的有限与无限的张力之下的克尔凯郭尔来说,他思想中那种不惜以毁灭自身为代价的突破自身的力量,使得真理与信仰的边界不再清晰,“真理—信仰”开始向着“实存”(existence)或“实在”(reality)敞开。没有创建自己的概念王国的克尔凯郭尔再一次沿袭了“思维—存在”的“概念工具”。他指出,真理的定义可以围绕“思维”(Tænken/thinking)与“存在”(Væren/being)的关系展开,但可以有从经验论角度和理念论角度出发的不同定义——经验论视角下的真理定义当表述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理念论视角下则为“存在与思维的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存在”,也就是思维与存在谁围着谁转的问题。克尔凯郭尔说:“如果在上述两种定义中‘存在’被理解为经验性的存在的话,那么真理本身就转变为一种被渴望的东西,一切都被置于生成之中,因为经验的对象尚未完结,生存着的认知者本人也处于生成之中,结果真理就成为一种接近(Approximeren),其开端无法绝对地设定,……”克尔凯郭尔完美地给出了在多元的当今时代人与真理关系的动态图景。在“回忆说”的语境中,人与真理之间构成认知关系,按福柯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人只要追寻知识或真理,就能获得之。在“道路真理”的语境中,人与真理的关系是个体永远追寻真理、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沿着克尔凯郭尔从经验论视角展开的真理定义,我们也渐渐靠近了经验论的古老真理标准,即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种种》当中所引用且赞同的英国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莫兹利(H.Maudsley)的标准——“人类共同认可,或者,为人类中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佼佼者所赞同”。与之相似,卡普托引用了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所说的“被普遍认可”(universally acknowledged)这一“聪明说法”,虽然卡普托指出,今天所认可的唯一普遍性就是多样性。
卡普托全盘接受了克尔凯郭尔描绘的个体永远走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之上的图景,同时将之放置于哲学史的背景之下,他把这种真理关系称为“爱真理”。“爱真理”而非认识真理,这个看法的提出既有基督教思想背景,又是向“爱智慧”的古希腊哲学的致敬。卡普托从现代性对宗教的压制出发,认为理性的自我规定是对信仰的排除,正是在这一点上他重提古希腊的“智慧”,认为它既包含了定义和论证,也包含了洞见和直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寻找“至上者”,也就是真、善、美。可以说,“智慧”折射的是广阔的生活世界,而非单纯的理论思维。“爱真理”的提出恢复了真理与激情之间的关系。
但是,仅仅“爱真理”还不够,“爱真理”不等于放弃对正确与错误的区分,那是无效的向“混沌”的回返。从与现代性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卡普托还指出,后现代性语境之下我们不谈论“纯粹理性”,而是谈论“好的理性”和“坏的理性”。这里的好坏之分没有道德意味,不评判动机,他说:“我们的意思只是有理与无理之间的对抗,可行与不可行之间的对抗。我们坚持认为,有些诠释比另一些更好,更有成效,更贴切。这不是相对主义,而只是承认真理如同生活一样是一桩冒险的事业。”
“爱真理”就要冒险,哪怕没有成功的保证,思想试验仍然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因为真理的“涌现”不受理性算计的掌控,用形象的语言说,真理的涌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用哲学语言说,那是因为“溢出和漂浮不定”是存在的规律。在全球化的、变动不居的当今时代,并不是每条道路都能通向罗马——“条条大路通罗马”再次成为一个自以为无限的有限世界的想象。为找到有效的道路,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概念操作,找到巴迪欧所说的“真理程序”,看哪条路能把我们更准、更快地带到罗马。
原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德法哲学》栏目“尼采论坛”专题。
推送时删减注释,如需查询,请参考原文。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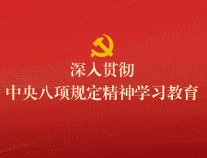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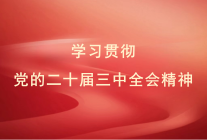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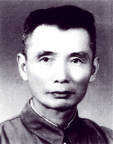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