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首页-
本所概况
哲学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 党建工作
- 研究学人
- 科研工作
- 学术期刊
- 人才培养
博士后更多+
- 图书档案
图书馆简介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 - 哲学系
【卢春红】从“怪诞”到“时尚”:西方美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野和过渡
提要:作为现代审美范畴,“怪诞”与“时尚”呈现出特有的结构,即通过形式所内含的对立彰显其与普遍性的外在关系。“怪诞”与“时尚”由此成为现代性的审美表征。在现代社会的总体背景下,“怪诞”与“时尚”因其不同的形式特征显示出关键性区分:构成“怪诞”之对立一极的普遍性是关联着理性的纯粹的普遍性;而构成“时尚”之对立一极的普遍性则是依托于感性的有限的普遍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由此在审美表征上呈现出各自的分野。在现代性的推进过程中,“怪诞”与“时尚”亦透露出内在的关联:由感性因素的出现到感性视角的转换,构成了由“怪诞”到“时尚”的关联平台。通过形式结构中“异”与“怪”的叠加,“怪诞”呈现的是普遍性实际上寻而不得的状态,这一审美存在由此显示出自身的过渡性质。而“时尚”则通过植根于变化中的“新”与“异”的交错,实际上建构着一种新的普遍性。于是,由“怪诞”到“时尚”,现代性得以完成其在审美存在中向后现代性的过渡。
伴随西方美学思想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其核心存在形态——审美范畴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比如,从形式结构的角度,“美”与“崇高”等范畴通常被归于传统,而“怪诞”(grotesque)与“时尚”等则被认定为现代范畴。然而,在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思想背景之间,人们通常对“传统之为传统”的理解较为明确,因而“美”“崇高”等审美范畴的传统归属也相对确定,带来麻烦与问题的是对“现代之为现代”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怪诞”“时尚”等审美范畴的归属问题。如果说作为传统社会之本质的古典性在结构上单一而明确,那么,构成现代社会之本质的现代性却因其双重结构而呈现出模糊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纠葛盖源于此。当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被视作一种延续时,其界线上的不明确需要得到分析与厘清。而当后现代性被认为是对现代性的反叛时,其内含的关联与过渡也需要得到梳理与阐明。本文以“怪诞”和“时尚”这一对现代审美范畴为例,尝试通过分析其形式上的双层结构来呈现西方美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野和过渡。
一、“怪诞”的形式结构:以彼此异在的方式彰显无关联性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怪诞”这一术语在西方思想中的源起可追溯至15世纪。据沃尔夫冈·凯泽尔(W.Kayser)出版于1957年的专著《美人与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怪诞”一词起源于意大利语“grottesco”,与“grotto”(洞穴)有关。大约15世纪末期,在意大利罗马城内一座叫作“尼禄金屋”的建筑地下室及走廊里,发现了一种当时人未曾见过的有着怪异风格的古代装饰画(这类画作后来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也陆续出现)。由于画作是在“洞穴”里首先被发现,意大利人便在该词基础上造出新词“grottesco”,来命名此类艺术作品。[1](参见凯泽尔,第8页)就“怪诞”风格的演进来看,在此后近代思想的变迁中,“怪诞”逐渐由一种装饰风格拓展为较为普遍的艺术风格,并作为“怪诞精神”(同上,第33页)与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文艺创作流派产生紧密关联。
由“怪诞”一词其内涵的发展过程可看出,这一风格样式实际上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呈现自身。一是作为一种装饰风格,“怪诞”指向一种特殊的艺术样态;二是作为审美范畴,它指向一种普遍的审美存在。前者处理的是具体艺术风格之间的关系。就这点而言,这一艺术风格可存在于历史的不同时期,如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怪诞风格的装饰画,而直到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这种风格的装饰画依旧是生活中常见的艺术存在。(参见刘法民,第1—41页)而作为审美范畴的“怪诞”虽然也含括具体的风格,却在根本上不同于后者,它指向的是审美存在的本质呈现,处理的是“怪诞”这一形式存在与普遍意义世界的关系。黑格尔以“阿拉伯式花纹”呈现建筑装饰中的怪诞风格(参见黑格尔,第59—60页)并非个案,而是沿续了西方近代思想一贯将“怪诞”的形式与“阿拉伯风格”相关联的传统。这也在深层上暗示着,“怪诞”之所以显得古怪,固然是因为它在具体形式上的变形或夸张,但更多地在于它从根本上外在于西方传统所接纳和认可的范围,并以此显示出自身的异在性。
1827年,维克多·雨果(V.Hugo)在后来被称作“法国浪漫主义宣言”的《〈克伦威尔〉序》中给予“怪诞”以重要定位,不仅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概念与类型予以肯定,认为“在近代人的思想里,怪诞(grotesquerie)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Hugo,p.26),而且对其审美特征作了具有代表性的描述:“一方面,它创造了畸形与可怕;另一方面,创造了可笑与滑稽。”(ibid.,p.26)[2]显然,该描述既显示出“怪诞”范畴所内含的形式结构的两重性,也预示了其内涵因关注重心的挪移而在近代思想中的变迁。
将“怪诞”与“滑稽”“可笑”相关联,多为雨果之前17—18世纪人们所强调。从形式角度来看,“怪诞”与“滑稽”都不符合生活世界中的正常存在状态。“滑稽”是对形式之正常状态的偏离,“怪诞”更是形式搭配上的古怪,由此呈现出“怪”(与正常形态相比)的特征。仔细考究之,“滑稽”在形式上的偏离本质上指向的是“丑”,它是由“丑”而怪;而“怪诞”的基本形式特征则是“异”,是由“异”而怪。在“滑稽”中,“丑怪”是局部的,形式的整体存在依旧与意义世界有着本质性关联,只是具体呈现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偏离,因而会引发“可笑”的感受。而在“怪诞”中,“怪异”不再是某一具体形式上的偏离,而是整体存在状态的异在。德国学者凯泽尔认为“怪诞是异化的世界”(凯泽尔,第195页),强调的正是其形式上的这一特点。在这一意义上,将“怪诞”与“丑”相关联抑或将之归属于“丑”并不准确。从狭义上看,“丑”之能够作为一种审美存在,呈现的其实是其对于美的陪衬。西方传统思想中,美所呈现的比例与节奏指向的都是对普遍性的完满呈现,“丑”虽是不完满的呈现,却也因陪衬而得以与普遍性相关联。就此而言,“丑”依旧可被归属于传统的审美范畴。从广义上看,“丑”之占据生活世界的主导地位,则意味着符合比例与节奏的和谐完满状态未能出现于意义世界。一个不包含普遍性的“丑”失去了作为其对照物的“美”,在这一意义上,“丑”不再作为“丑”而存在,它在本质上已成为“怪”。
换言之,“怪诞”之所以被称作“怪”,并不单纯是形式上的变形与夸张,而在于通过这一变形与夸张呈现出来的与普遍意义的特定关系。在丑的样态中,形式与普遍意义之间固然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却也因为这一对立而与普遍意义产生关联。在传统的审美世界中,“丑”之处于陪衬地位并不是对“丑”作为审美范畴之重要性的贬斥,而恰恰是在强调其通过美而与意义世界的间接关联性。鲍桑葵特意指出,“丑是艰难的美”(鲍桑葵,第48页),强调的正是“丑”与“美”的特殊关系。“丑”虽无法做到像“崇高”那样,以形式之“无”而打破形式自身的限制,直接与普遍意义世界相关联,却也借助“美”而获得与这一普遍意义的关联。但是在“怪诞”中,形式之所以不合适却不是因为其与普遍意义的对立,而在于与这一意义世界彻底切断了关联,成为一个全然外在于意义世界的存在。
从19世纪开始,“怪诞”更多转向与“畸形”“可怕”相关联,便是这一“异”的层面逐渐受到关注与重视的结果。如雨果的界定所暗示,可怕的事物在形式上指向“畸形”,这表明其针对的并不是具体存在,而是普遍性的生存样态。在这一样态中,“畸形”表达的是对整体意义的彻底破坏。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曾将对这一状态的感受称作“畏惧”,并指出,日常生活中我们怕的是具体的事物,而“畏之所畏者”却并非某一事物,而是“在世本身”;“畏惧”的感受正源于我们面对的是生存的全然无意义状态。(参见海德格尔,第213—220页)由此,“怪诞”因为与“可怕”的关联而和“滑稽”有了明显区分。
不过,凯泽尔虽然着力强调“怪诞是一场同荒诞的游戏”(凯泽尔,第198页),给人们带来的是绝望与恐怖,却依旧在“怪诞”的形式结构中给“可笑”与“滑稽”留下了必要位置。个中缘由当然不只是对19世纪雨果所作描述的简单回应,同时也是“怪诞”这一范畴在其形式结构上的本质要求。“可怕”“恐惧”的感受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其所呈现的只是纯粹的“无”。在这一意义上,“畸形”在形式上指向的其实是单一结构,即不仅切断了形式与意义世界的关联,而且这一被切断的意义世界已全然不在场,形式所呈现的只是无。与此相对照,“怪诞”却有自身的特殊性。通过形式所呈现的异在性,“怪诞”意图强调的则是形式与普遍意义的同时在场,差异与不同的前提与基础是对照,因而必得先有对照的双方。只不过在这一对照中,普遍性虽在场,却是以与形式全然无关的方式呈现。与“丑”相比,“怪诞”显然在切断与普遍依据的关联中行走得更为彻底,以至于完全没有了“美”这一中介环节出现的可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普遍的意义世界就此消失。在丑的形式中,普遍意义没有消失,在怪诞的形式中,这一意义世界依旧存在,切断的只是关联线索。彻底失去与普遍意义的关联后,形式的存在因为其全然无法理解而成为格格不入的存在,怪诞的感受正由此而来。在这一意义上,“怪诞”虽然与“可怕”“恐惧”相关联,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可怕,因为还有异在的普遍世界矗立于眼前,怪诞形式的无意义只能将自身呈现为“异”中之“怪”。
至此,“怪诞”在其双层结构中呈现出其与意义世界之间的特殊关系。作为一种审美存在,“怪诞”通过形式结构首先凸显的是其与普遍性的全然无关性,这构成“怪诞”之为“异”的内在本质;同时,它也以异在于意义世界的方式将这一世界带上前来,这构成“怪诞”之为“怪”的深层背景。
二、“时尚”的形式结构:以彼此异在的方式构建关联性
在西方思想中,“时尚”这一术语的源起几乎与“怪诞”同步,亦可追溯至15世纪。依据日本学者川村由仁夜(Yuniya Kawamura)在其专著《时尚学:时尚研究导论》中所作的词源学概述,英语中的“fashion”(时尚)一词来源于拉丁文“facio”或者“factio”,意思是“making or doing”(“制作”或者“做”),转变为名词后,其意义延伸为“一种特别的造法或形状”,主要是指生活方式或着装打扮上的流行风格或样式。(see Yuniya Kawamura,pp.3-4)由此可见,“时尚”也有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一是作为服装的流行式样,涉及具体的装饰形式;二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存在,指向生活方式中的时尚。
就前者而言,一般认为服装中的时尚最早起源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初期之间。人类装饰自身的需求自古就有,而且古代人的装饰并不比现代人简单,甚或更为复杂。但是在古代世界中,这些装饰大多是一种身份或者地位的象征,与时尚并无本质关联。大约15世纪前后,人们对服装装饰的关注点与之前相比有了不同,比如“富有新意的剪裁、新鲜的颜色和材质开始涌现,肩部与胸部的宽度开始出现变化”(史文德森,第18页)。到了16世纪,“由于根据个体身体轮廓而量体裁衣,……使得服装变化本身成为一种愉悦的因素”(同上,第18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服装制作上的突出特征就是对“变化”的认可。这不仅体现在服装的具体组成因素上,而且显示于整体服装的风格中。换言之,“变化”构成了服装时尚的内在特征。这对于“时尚”概念的出现显然是一个重要基础。服装之所以花样繁多,其内在基础是“变化”,变化才能够真正带来不同。关键之处在于,究竟什么意义上的“变化”才构成真正的变化?在古代,人们的服饰即使不是频繁变化,也多少会有区分和不同。现代社会虽然加剧了这一过程,但量上的差异并不足以具有本质意义。由此,我们将“时尚”在当下生活中的出现归结为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仅指出了变化的表征,尚未涉及实质。正是在此意义上史文德森强调,不是所有的生活方式的变迁都可被称作“时尚”。(参见同上,第5页)具体的时尚研究大可以对时尚的流行趋势作整体追踪,并由此得出流行风格在其变化中也会出现一种似曾相识的周期性回归的结论,却未能从根本上切中“时尚”的本质。相反,这一现象恰恰说明,局限于具体事物,“变化”的产生带来的同时也是“变化”的终结。
真正使变化成为变化的深层依据在于,其参照物不再是具体事物,而是整体的意义世界。在“时尚”还停留于服装的具体风格时,“变化”虽呈现的是具体服装样式之间的不同,却也未曾离开整体生活世界的背景,与具体服装样式的对照同时也是与整体生活世界的对照。在这一意义上,作为脱胎于服装的审美概念,“时尚”不再局限于服装,也会扩展到语言的使用、礼仪等领域,普遍化的结果使得“一时之尚”脱离对具体样式的描述,而成为这一审美状态之本质性状的展示。康德指出,“一切时尚按照其概念就已经是变化无常的生活方式”(康德,第239页),强调的其实是作为普遍存在方式的“时尚”。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时尚”与其意义世界之间的关系得以展示。在古代世界,具体的事物、生活虽处于变迁之中,普遍的意义世界却不拥有变化的因素。由此,美之为美的具体形式固然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具体的关系与比例也有不同,这一不同却不被称作“变化”。到了近代世界,普遍的意义世界不再是永恒的,它通过与感性世界相关联而内含变化的可能性。由此,“时尚”要使自身成为变化中的存在,首先需要与普遍的意义世界产生断裂。唯其断裂,方能拥有获得变化的可能。因此,“时尚”在形式结构中首先呈现的是其与普遍意义世界之间的外在关系,它正是经由这一外在关系而获得自身的现代性。在与意义世界之绝对区分的意义上,这一不同被称作“异”。具体的不同涉及的是具体事物之间的区分,而“异”作为绝对的不同指向的是形式全然外在于普遍意义。
于是在外在于普遍世界的意义上,“时尚”与“怪诞”拥有了相同基础。“怪诞”通过形式上的古怪显示出其对于普遍意义世界的外在性,而“时尚”则是通过变化显示出其与普遍意义世界的断裂。相对于“美”,“丑”在形式上也呈现出与普遍意义世界之直接关系的断裂,却又通过“美”而获得一种间接关联,因而,“丑”并不真正外在于意义世界。“怪诞”与“时尚”却有自身的特点,它们的形式结构所呈现的不仅不同,而且是绝对的“异”,全然切断了其与意义世界的关联。不过这也意味着,仅仅显示出绝对的“异”并不足以让时尚成为时尚。如前所述,“怪诞”除了表明自身与普遍意义世界的异在性关系之外,还通过“怪”彰显其与意义世界的不相关性。“时尚”也同样如此。除了变化所要求的与普遍意义世界的外在性之外,“时尚”概念还呈现出另外一层内涵,即形式上的新颖。此处并非意在强调其与“变化”的区分,恰恰相反,“新颖”以变化为前提。因为有变化,“新颖”才得以呈现自身。不过变化可以带来不同,却不必然呈现“新颖”。将变化所呈现的不同与“新颖”相关联,表明这一形式在不同之上还拥有新的规定。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规定?
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以时间为线索将新与旧相对照,旧的事物界定为时间上在前出现,而新的事物则是时间上随后而来。不过,基于时间的对照并未切中问题的实质。如若面对的只是具体事物,并没有充分依据将后出现的事物称作新,能够呈现的最多也只是不同和变化。因而,只有当“时尚”所面对的不再具体事物而是普遍存在时,新的形式方能呈现自身的本色。在与普遍意义世界相对照的前提下,如果说形式是“新颖的”,则传递出一个重要特征:“新”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建构了它与普遍意义世界的关联。形式之所以能是新颖的,固然在于它是普遍意义世界尚未含括的存在,更是因为这一意义世界因缺少这样的存在方式而需要它,新的形式正因此而被接纳。康德在强调“新颖就是使得时尚惹人喜爱的东西”(同上,第239—240页)时,虽不免流露出伴随理性视角而来的对时尚的鄙薄之意,却也借由“喜爱”道出了形式与普遍意义因接纳而关联的深层事实。在面对具体事物时,新与旧的对照指向的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外在关系,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旧的事物将会被取代,而当时尚以新的形式面对普遍意义世界时,“新”的出现揭示的反而是两者之间的一种内在关联。
于是,基于这一内在关联,“时尚”与生活中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流行”的关系亦显示出本质意义。人们常常在日常生活的意义上将“流行”理解为对于时尚事物的模仿。归根结底,这其实是我们在面对具体事物时的一种感觉错位。作为一种普遍的存在,“时尚”真正面对的只会是普遍的意义世界。对于时尚形式在经验层面的模仿实际上显示了对其在先验层面的接纳。在本质意义上,时尚的事物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时尚”通过“新颖”建构其与意义世界的关联。时尚的东西之所以必然流行,则是因为这一关联性存在于“时尚”之形式的内在结构中。新从来不与旧形成对照,可以不新、不流行,却不会成为旧的。时尚不再是新的是因为它已经融入到意义世界之中,时尚不再流行则是因为它需要接纳新的形式。
至此,“时尚”的形式结构也显示出自身的两层内涵。作为带来变化的形式,“时尚”以自身的“异”从根本上外在于普遍意义世界;作为一种引起流行的形式,它又以自身的“新”建构起它与普遍意义世界的关联。
三、“怪诞”与“时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何以分野
对形式结构的分析表明,“怪诞”与“时尚”作为审美范畴拥有相同基础:其形式存在外在于普遍意义世界,与其呈现出“异”的关系。它们以此与传统的审美范畴相区分,后者始终内在于这一意义世界。不过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两种不同的关系何以产生?
追问不同关系的存在缘由,指向的是对作为其背景的思想的探究,也由此涉及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在西方传统思想世界中,普遍意义的呈现是单一的,只以纯思的、逻辑的方式进行,并不与感性的存在打交道。苏格拉底以“精神助产术”开启了这一行程,柏拉图则通过对理念世界的命名让普遍性获得独立。至亚里士多德,“质料”虽然是作为理念的形式之外的另一个因素,却依旧是思维的对象,与感性全然无关。传统思想的这一精神无疑构成传统审美范畴呈现自身的底蕴。作为审美存在,美必然也拥有自身的感性形式,但这一感性存在与现代社会中的感性存在相去甚远,后者所内含的时间维度使得感性存在具有本质的当下性,而前者则是顺从理性规定而来的感性,它以这一特殊方式使自身成为抽象的、不具有感性本色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美必然与普遍意义世界产生深层契合。
与此相对照,现代社会显示出根本性差异。不同于传统思想中理性存在的单一性,现代社会在理性规则之外,还接纳了个体因素。古代思想主要通过纯思获得对普遍性的呈现,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还将这一呈现与人的感性存在相关联。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肇始于中世纪。在基督教神学思想的浸染下,理念通过普罗提诺“太一”的转化并借助上帝身份获得自由本性后,终于显示出古希腊哲学尚未达到的纯粹性,也真正得以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然而,也恰恰因为这一纯粹化,通过现实世界来获得自由的呈现反而成为理念的一个内在需求。这一变化的现实契机出现于18世纪。伴随近代思想的主体转向和对心灵诸种能力的探究,当“形形色色的精神力量汇聚到了一个共同的力量中心”(卡西尔,第3页)时,“理性”一跃成为这一世纪的核心术语。正如卡西尔所指出,作为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理性“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上,第3—4页),因而成为这些精神力量之本质特征的体现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借助康德先验哲学体系的层层审查,普遍规则得以通过理性进入主体,与感性因素共同建构了现代意义上的人。于是,对人的启蒙成为理性的根本要求,也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总体背景。发端于17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虽涉及诸多领域并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其思想的内在根基指向的却是“启迪蒙昧”。这就意味着,启蒙的出发点不是理性存在,而是感性个体,是由感性出发向着理性推进,社会的发展亦由此落实为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
然而,将个体因素引入现代社会,虽使得主体意义上的人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心,却也让“如何处理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成为时代的核心话题。理性虽能进入主体,其本质却是纯粹的自由,感性表征着人的真实存在,却也因此受制于这一存在。康德通过先天综合判断将理性与感性两个因素纳入其中,并由此提出了综合的任务,这就引发后来思想从理性与感性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沿着理性的思路切入,黑格尔以精神的方式展开纯粹理念的现实化过程,目的是让理性走出自身,获得现实内涵。然而,当这一融合是以扬弃的方式进行并呈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时,在康德那里尚显含混的综合显示出自身的特质:以含融对立的方式获得统一。顺着感性的路径前行,席勒以游戏冲动的方式展开获得人性的教化过程,目的是让感性能够走出自身,朝着理性迈进。然而,当这一融合是以扬弃的方式呈现时,综合依然显示出相同的特点。如席勒所强调,保存这一绝对的对立,恰恰是人性作为整体而呈现的必要前提。(参见席勒,第142—143页)显然,无论是从理性角度还是感性角度,近代思想在面对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时,都是以接纳对立来达至两者之共处一体。
思想在近代以来所呈现的变化无疑构成“怪诞”与“时尚”得以呈现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这两者的形式结构均呈现出由外在性而来的形式与普遍意义的根本对立,而这一对立正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在审美存在中的呈现。就此而言,将这两个范畴归入现代审美存在有合理且充分的依据。不过到此为止,我们只是分析了这一对审美范畴所呈现的形式结构,尚未展现感性存在与普遍意义之间的本质关系。恰恰是在对其关系的关注中,两者之间显示出关键不同。“怪诞”之所以为“怪”,固然在于它对于普遍意义的绝对外在性,更是因为当形式与普遍意义相关联时,形式不得其门而入的失败尝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时尚”之所以为“新”,恰恰在于形式与普遍意义相关联时,普遍意义对形式的接纳。将这一差异与深层的思想基础相关联,揭示的则是现代社会的另一层转化。
思想迈入现代社会后,感性与理性的彼此外在性所带来的两极张力从感性与理性两个不同层面显示出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站在理性的立场,鸿沟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观念并不产生实质性影响,而黑格尔精神发展的宏大历史过程最终能够回到理念自身,能够将绝对理念的内涵展示出来,正在于感性这一外在于自身的东西终究是被扬弃的因素。而从理性立场转向感性角度,其中存在的问题立刻显示出来。席勒在对人性的教化中指出,从感性出发绝无可能达至理性,进而完成“把使感觉同思维、承受同能动分离开来的那条鸿沟填平”(同上,第150页)的任务。这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因而,一旦叔本华从纯然生存意志的角度来关注这一感性世界,普遍意义的虚无必定会成为一种基本的生存感受。换言之,认为人可以不断突破感性限制,最终成为理性意义上的人,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进步最终也必将实现理想目标,其实是理性所带来的幻象。“怪诞”之所以被称作“怪”,也并不只是因为其与普遍意义的彼此外在性,而是因为,一旦这一对立是绝对的,那么从作为审美存在的形式入手,便无从找到进入普遍意义的路径。
果真如此,“时尚”又如何呈现其形式与普遍意义的关联?这就涉及近代西方思想在推进中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而言,尼采在19世纪末宣称的“上帝死了”拥有复杂的诠释维度。站在19世纪的思想立场,当尼采从感性角度说出了一个本应直面的现代性事实时,这一宣称未免带有浓重的悲观情绪,普遍意义的消亡也一度导致虚无主义的蔓延。这确实构成世纪之交的一种时代表征。依据20世纪的思想特质,尼采的这一宣称却不无积极意义。上帝的不存在并非是不再需要一切规定,而是意味着不再需要由上帝而来的理性规定,转而由强力意志来“重估一切价值”(尼采,第65页)。至胡塞尔,这一层积极意义才获得理论上的支撑。依据现象学的本色,“本质的直观”的获得是因为主体的纯粹意识原本拥有一种意向性结构。(参见胡塞尔,第51—53页)由是,感性便不再是被动的,而是自身就能呈现出特殊的构造能力;由此亦带来一种新的“本质”,即可被感性把握的本质。此后的海德格尔更是彻底,按照存在论的要求,他将主体内部的“本质”转换为生活世界中的“存在”,认为“存在”就是对存在的领会。(参见海德格尔,第7页)当伽达默尔经由观赏者的角度分析审美经验时,凸显的是观赏者与游戏活动完全的外在性,存在却恰恰因为这一外在性而与“此”同在,(参见伽达默尔,第175—179页)并通过“此”对存在的理解而将存在之真理展开为有效应的历史。新的普遍性由此呈现自身的现实内涵。回顾这一发展过程,从其彻底消除纯粹普遍性的意义上,思想显然已经由现代性进入后现代性,从传统世界中延伸而来的纯粹普遍性至此销声匿迹。然而,“破”的过程同时也是“立”。打碎了理性意义上的普遍性,带来的却是与感性有关的普遍性。
落实于审美存在,“时尚”通过自身的另一形式特征呈现出这一变化的本质。从此前的分析可知,新异是时尚的主体内涵,“异”规定了其形式结构,“新”建构起诸因素间的关系。然而,“时尚”之所以不被称作“新异”而被称作“时尚”,在于其所内含的一个基础特征——“变化”。“时尚”固然是以形式的方式呈现自身的存在,这一形式却与变化内在关联,即形式是一种处于变化中的形式。只不过,与“时尚”的形式特征——“新异”相比较,“变化”指向的是另一层关联。如果说“时尚”与“怪诞”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作为“新异”体现出与普遍性的关联,那么“变化”通过“流行”指向的正是普遍性的建构。正如西美尔所言:“时尚是对既定形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西美尔,第72页)从本质上讲,“流行”的内在本质是模仿,后者根源于“需求”,指向的是“接纳”,它通过呈现流行的效果,得以完成普遍性的建构。
显然,在“时尚”通过新异的追求将自身体现为变化的过程中,“流行”是一个内在要素。此前本文曾分析了通过“流行”所呈现出来的普遍性的态度,即对“新颖”的接纳。这是一重要前提,却并非“流行”概念的全部内涵。“流行”之所以构成“时尚”的内在要素,固然在于其对“新异”的接纳,更在于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正是通过“流行”这一接纳方式,新潮的东西不再新潮,独特的东西变得趋同。换言之,“流行”通过对“时尚”的接纳,恰恰让曾经新异的东西不再新异。另一方面,“流行”之所以接纳“时尚”,目的是为了“变得时尚”。(参见史文德森,第18页)这意味着,“流行”通过这一渴望成为“时尚”发展的动力。两相结合,“变化”的真正内涵显示出来。“时尚”固然展现出与传统的不同,却不是“对传统的摒弃”(同上,第19页),而是带着传统一起前行,“新”的普遍性存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呈现。对于“怪诞”而言,普遍性并不与形式相关。“时尚”却不同。站在感性角度,“时尚”的形式虽也难以企及纯粹的普遍性,却通过形式所依赖的变化而呈现出新的普遍性,即有限意义上的普遍性。
于是,通过“怪诞”与“时尚”各自形式所呈现的对于普遍性的不同规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界限得以明晰化。如果说感性因素的加入以及感性视角的确立是我们进入现代性的前提,那么正是两种不同涵义的普遍性构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野。
四、从“怪诞”到“时尚”——现代性如何通向后现代性
然而仍需追问的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果真泾渭分明么?站在普遍性的角度,显然如此。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普遍性,前者指向的是纯粹的普遍性,后者关联的是有限的普遍性。不过,一旦从普遍性视角转向感性视角,由现代性通向后现代性的可能性亦恰恰由此彰显。
从传统世界进入现代世界,感性的加入并不只是意味着增加了新的因素。感性与理性的彼此外在性决定了两个因素的并立实质上是过渡阶段的一种表征。在这一意义上,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真正深刻之处并不在于实际解决了什么问题,而在于开启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纯粹感性因素的出场由此成为带动整个思想范式转换的前奏。甘丹·梅亚苏(G.Meillasso)在将康德思想的这一特点称作“‘较弱的’相关主义”(梅亚苏,第70页)时,意图肯定的正是康德的这一洞见。由此,将感性作为一个被动的、有待规定的状态,只是理性在面对感性时一种来自思想传统的优越感的表现。一旦将这一思路贯彻到底,便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理念虽然得以拥有感性内涵,感性却也因此离开了“自身”,丧失了其作为感性的独立性。以理性为主导的综合,终归要付出感性的代价。感性存在固然难逃自身的局限,却不意味着感性需要以及能够最终摆脱自身以获得纯粹理性的存在。就根本而言,感性从无可能离开自身的有限性存在。席勒对审美状态的描述表明,感性的上下求索带来的依旧是“生存最高的丰富性”(席勒,第105页)。
于是,当理性陶醉于自己所描绘的光明前景时,感性存在于默默中开启了属于自身的征程。席勒虽然还将感觉定位为“被动性”,却也通过“游戏冲动”展示出属于感性的“自由心境”。(参见同上,第162页)当理性还在面对自我的没落而自怨自艾之际,感性存在早已逐步凸显自身主动性、创造性的本色,尼采的“强力意志”更是通过“永恒轮回”在与上帝的对抗中迸发出现实人性的光辉。无怪乎哈贝马斯声称,是尼采“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哈贝马斯,第121页)。也正是因为与理性彻底决裂的态度,哈贝马斯认为,《悲剧的诞生》“这部思古的现代性的‘迟暮之作’变成了后现代性的‘开山之作’”(同上,第100页)。理性按照自己的理念不懈地对感性进行启蒙,却未曾想到有朝一日感性不再跟随理性的教导贬抑自身,也不会因为理性的退场而惶惶不可终日,“迷茫”只不过是感性因依赖而产生的短暂不适,时间证明,感性终究会安身于有限的存在,去追寻诗意的栖居。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于生活世界中追问“艺术作品的本源”,艺术存在通过世界与大地的争执将自身呈现为真理的发生,由此奠定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在这一意义上,丹尼尔·贝尔(D.Bell)强调后现代主义就是比现代主义更现代的“主义”有其合理且充分的依据。当我们将关注重心由理性而转向感性,借助这一感性视角,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思想上的延续性毋庸置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由前者走向后者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现代性之所以显示出与后现代性的不同,实质上是因为,现代性并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社会,传统的理性精神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现代性。因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冲突,实际上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在现代社会中的折射。在这一意义上,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并非一帆风顺,在先破而后立的工作中,首先需要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而后方能开启现代社会自身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的作用由此凸显。贝尔指出,“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它把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贝尔,第98页),其强调的正是后现代主义的推进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为的是从各个层面向理性发起挑战。德里达提出的“彻底地解构理性”乃是这一思潮的极致,其目的在于打破伴随传统而来的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
但如果因此而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理解为对普遍性的摧毁和对感性的关注,站在传统的普遍性角度,这一说法依旧有其自身的顾虑。相对于现代性在其张力结构中对普遍性的保存,后现代通过消除普遍性彻底斩断了与传统的关联。而如果没有新的普遍性被建构,后现代性的消极意义显露无遗。然而,恰是在这一后现代性的激进与彻底中,当理性的威压不复存在时,一种新的普遍性得以呈现出来,而现代性中处于张力之一端的纯粹的普遍性则因其实质上的无从获得而渺无踪迹。换言之,如果说从传统到现代是理性在走出自身,那么从现代到后现代则是感性在回归自身。而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大体上都行走在这一回归感性自身的过程中。后现代性则是用特殊方式推进了这一行程,从而最终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真正进入了现代社会。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层面在进行“先破后立”的推进工作时,审美存在也从形式角度将现代世界的本质性转化过程呈现出来。无论“怪诞”,抑或“时尚”,现代审美范畴在形式结构上不同于传统审美范畴的根本之处在于,传统审美范畴中的形式内在于普遍性之中,而现代审美范畴中的形式则呈现的是与普遍性的异在关系。不同的关系势必会对形式自身的特点产生影响。在传统的审美范畴中,形式之能够内在于普遍性,在于这一形式是被思维所规定的形式,已被抽离了感性的内涵。与此相对照,现代审美范畴中外在性的另一层意义展现出来。在“怪诞”与“时尚”中,形式与其普遍性的绝对对立,无论这一普遍性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表明的都恰恰是形式的感性特质。换言之,形式正是通过这一对立而返回审美存在的感性本色。然而,对立不只是显示出这一感性特质,当形式因为这一对立而无从获得自身的普遍性时,便意味着“怪诞”还在这一对立中转换了视角。从普遍性视角审视,“怪诞”的形式至多是一个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全然无关的存在,呈现的只是“异”;从形式自身的角度,“怪诞”不只切断了与普遍性的关联,还揭示了自以为存在的普遍意义在现实层面形同虚设的性质。换言之,此前所分析的“怪诞”形式的两个特点,其深层内含实质上是视角的转换,由“异”到“怪”显示的正是由普遍性的视角转向形式的、感性的视角。
由感性特质到感性视角,这是两个相互关联却又彼此不同的阶段。如果说前者构成了“怪诞”与“时尚”相关联的内在基础,后者则显示出“怪诞”之走向“时尚”的现实情形。从感性的视角来看,“怪诞”之不得其门而入的状态表明,在“没有意义呈现出来”的意义上,“怪诞”并没有完成对现代性的审美建构。在这一意义上,“怪诞”注定是一个具有过渡性质的范畴,它因为这一过渡而打开了通向“时尚”的可能性。同作为现代性的审美存在,“时尚”的形式结构也呈现出根本的对立性。从形式自身的角度看,处于变化之中的形式呈现的并非具体形状的不同,而是与普遍性相对照而言的根本性的“异”;从普遍性的角度看,这一形式即使不是“怪”,而是会被模仿并产生流行的“新”,也并不改变其外在性的本质。然而这并非是说,“时尚”的形式结构也会带来一种由普遍性向着感性的转向。其形式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感性的底蕴,它不只是一种新异的形式,还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形式。如西美尔所言:“时尚的问题不是存在(being)的问题,而在于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non-being);它总是处于过去与将来的分水岭上,结果,至少在它最高潮的时候,相比于其他的现象,它带给我们更强烈的现在感。”(西美尔,第77页)“时尚”的存在之所以是变化的,在于“时尚”与时间的一种本质性关联,其所呈现出来的永恒的“现在感”充分表明其内在的感性本色。“时尚”也始终立根于感性的视角。其形式结构虽然也呈现出形式与普遍性之间的外在性,但这一外在性呈现的却不是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形式之能够以“新”的方式为普遍性所接纳,表明普遍性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纯粹的与理性相关的普遍性,而是与感性相关的以有限的方式呈现自身的普遍性。在这一意义上,“时尚”无须进行视角的转换。
在无须转换视角的意义上,“时尚”的另一层意义彰显出来。变化中的形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结构,它走出普遍性之外,固然表明了自身与普遍性的根本外在性,深层目的却是为了普遍性自身的建构。“时尚”所立足的现在并非纯粹的转瞬即逝的现在,它之所以“处于过去与将来的分水岭上”,在于它以这一特殊的方式关联着过去与将来。变化中的“时尚”以“异”的方式走向将来,又以“新”的方式带着过去,它以这一方式呈现出变化中的普遍性。于是,在“怪诞”之中未能完成的现代性建构终于在“时尚”之中得以呈现,不过却是以后现代的方式完成了的现代性审美建构。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世纪西方思想中三条思路的交汇与美学的逻辑建构问题研究”(编号21BZX025)的阶段性成果。
[1]对于这一术语的词源学梳理,本文还参考了贡布里希出版于1979年的专著《秩序感》(参见贡布里希,第305页)和刘法民出版于2000年的专著《怪诞——美的现代扩张》(参见刘法民,第46页)。
[2]译文参见《〈克伦威尔〉序》。(参见雨果,第33页)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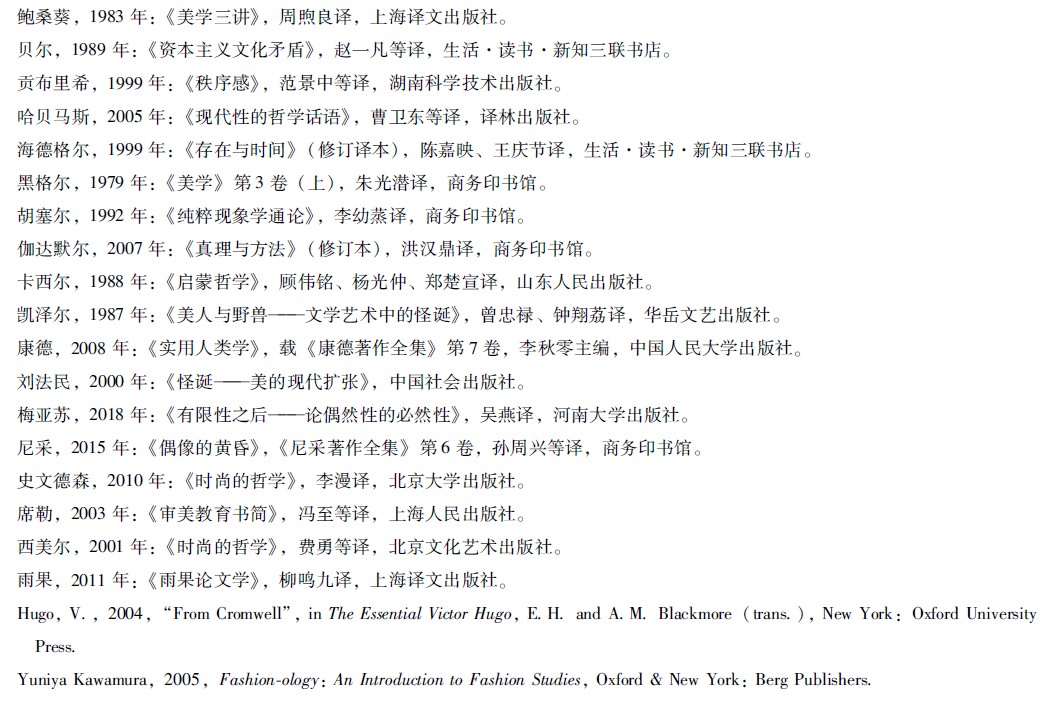
原载:《哲学动态》2022年第8期
来源:“哲学动态杂志”微信公众号2022-9-2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 电话:(010)85195506
电话:(010)85195506
![]() 传真:(010)65137826
传真:(010)65137826
![]()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












